
(一)
母亲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初五,自从三十年前离开家乡小村,每年这一天,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回来,家里像过节一样。随着年龄增大,一年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心中也想着常回家看看,但都会被一些“冠冕堂皇”的事务夺走了时间,转眼母亲已经八十三岁了。
春节回家过年,已经感觉到母亲的苍老,雪白凌乱的头发,满脸粗糙的皱纹,步履亦带蹒跚。过去精明能干的母亲,如今面对蒸糕、和面、包饺这些年活儿,只能望洋兴叹了。我知道,母亲的未来日子越来越少,我报恩的日子越来越短,这样想着,猛觉着一阵阵惭愧,涌上了心头。
刚刚进入三月初一,父亲的电话就一天两次打来,提醒我母亲的生日就要到了。其实我知道,这不是父亲主动打来电话,而是母亲在家中开始唠叨此事了。当天我办理了休假手续,准备长时间地陪伴父母一段时间。亲情的表现,有时不仅是衣食供给,更是一种温馨的陪伴。
我购买了初二傍晚的高铁票,并打电话告诉家中,当我辗转回到家中时,父母都没睡,坐在灯下等我,锅里还热着饭,床上新被套早已铺好。“娘,我回来了”,游子一句简单的话,满屋子早已洋溢着无限亲情。
这就是家,一个不大却给予我温暖的地方,幼年,少年,小学,中学,我就是从这里背起行嚢,告别乡亲,走出垄野,带着诗与梦想奔向远方…
这就是家,小门,小院,篱笆墙,小村老家一切还保留着我小时候的模样…唯一变化就是我二十年前种下的几颗幼竹,如今已经苍翠挺拔,密集绵绵,它们矗立于草门边婷婷玉立,守望着我的家,还有我的老娘…
(二)
我的家乡小村,以最先创村的姓氏而命名为周家庄。传说祖上是兄弟二人,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至我这辈,已达二十一世子孙,历经了四百余年发展,目前繁衍成四百户人家的村庄。
我的小村,离渤海南岸的羊口渔港码头仅二十公里,春夏时节,日夜温差较大。昨日返乡的疲劳,也让我自然美美地睡到清晨。我从庭树鸟鸣中醒来,闭着眼睛享受窗风微寒抚面。小屋一人的世界里,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坦然,好似外部的一切,离我那么遥远,那么遥远……“起床吧,饭都凉了”,母亲轻轻喊着我的乳名,犹如梦幻般稚童时的呼唤。我睁开眼睛,母亲几乎贴着我的脸,慈祥地凝望着我。也许在我床头,母亲已经坐了很久很久了。
我努力回忆着,母亲予我的最原始记忆,一点一点地向灵魂深处挖潜,这时浮现出二岁半时的影像,妹妹刚刚出生,家里远亲近邻人来人往,只见三姨提来一条刀鱼,看望哺乳期的母亲,大人笑着,说那条鱼比我还高。二岁半,对母亲当时的言谈举止,已经模糊不清。只记得,我呆在三姨怀里,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大人们塞到嘴里的东西。
如今,农村物质文化生活已丰富多彩。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打出,附近的酒店就会送来“量身定做”的美食,菜堆满案。虽说走南闯北,也吃过百家之饭。然而我对家乡饮食有种百吃不厌的偏爱。这方水土,养育我走过童年少年时代,那种根植灵魂深处的故乡之情,也将陪伴我走过终生岁月。
(三)
我清早起来,走出村落,迎着朝霞,信步踏入尺许些高的青青麦浪之中,去感受那浓浓的乡村春意。小时候的曾经流水潺湲的沟渎池塘,里面长满了芦苇杂草。我还记得昔时渠沟两畔,杂樨荆棘高过人头,这是小孩子们捉迷藏或玩游戏的最佳场所。过去农村没有幼儿园,这些荒坡野地就是孩子的快乐天堂。
玩累了,大伙就商量些坏主意,如何去破坏大人的劳动成果?或者采摘尚未成熟的花果,或者偷吃涩涩苦口的李桃。记得前邻三奶奶院中有棵枝蔓茂盛的葡萄树,葡萄刚刚挂果的时节,三奶奶总是坐在葡萄架下,大声喝叱我们这些探头探脑的小孩儿。但我们总能趁着三奶奶洗衣做饭的空档,迅速作案,然后一哄而散。三奶奶是非常善良的老人。中秋节葡萄成熟时,她都会剪下几串,分到各个家中,品味三奶奶家的酸中带甘的大葡萄,也成为我童年难忘的记忆碎片。
清贫的年代有清贫的快乐,儿时的时间总是那么漫长。每天傍晚,我就站在村头最高的地方,盼望着参加集体劳动的母亲早些归来。小孩的视野很小,也许孩子眼中最温暖的世界就是母亲的怀抱。
(四)
多少年来,母亲对于生日仪式并不看重,对满案盛食也无多少兴趣。只是每次我们回来,她就一直笑着,慈爱的目光似乎不曾离开过我们的身影,我知道母亲守望的就是儿女的回归,哪怕是短暂的相聚,母亲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记得父母对我祖父母一直敬重有加,祖父祖母生日,母亲不仅献上煮蛋,父亲还要对祖父祖母行跪拜大礼。今天这些“繁文缛节”在我辈已经省略。母亲生日,我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几日温馨的陪伴而已。而母亲对于儿女的生日却格外寄重,小时候,即是日子过得再紧,每逢孩子们的生日,母亲都会煮上一只鸡蛋,看着我们吃完,多少年来,吃上一只完整的煮蛋就成为了我们乡村小孩的生日标志。即便人到中年,在我生日这天,母亲依然让父亲打来电话,嘱咐我要吃一只鸡蛋,寓意一岁的圆满与顺利。人间的亲情是什么?是一杯递来的茶水,是一句简短的问候,是一双凝望的眼睛,是对坐无言的默契,是一段静静的陪伴。也许正是这些最平常不过的简单与纯朴才是人间最真实、最温暖的地方。
(五)
母亲生日,正赶上谷雨时节,天地氤氲,竟然绵绵密密地飘下雨来。我仰着头,望着乌蒙的天空,任细雨清凉润面。阵阵东风吹得庭树摇来荡去,院中父母亲种下的几畦青菜,却尽情沐浴于甘露之中。
我家老屋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显得古朴沧桑,并不明亮的老房灯下,父亲看着旧书,母亲静静地独自端着茶水,一只花猫安然睡在沙发的最深处。
小院南面的一棵古槐,两颗枣树,好似在我小时候就这般高,如今依然苍翠丰茂。据父亲讲,院中这颗老枣树他小时候就已很大,这样算来,已在我家历经百年风光了。
我的祖上应算诗书之家。祖父在民国时期正上师范时,恰逢日本侵华,祖父的老师带领包括祖父在内的大部分学生集体参加了国家军队。祖父在世时,还经常给我们讲些他的生死经历的故事,祖父九十三岁去逝,逝前留下了近十万字的回忆录。
(六)
农历三月初五,正是母亲的生日。这天清风徐徐,莺鸣传堂。一大早,村委两名干部就送来了喜庆的蛋糕。这是村子里八十岁以上老人都享用的福利。母亲的生日在村南弥河北畔的一家小酒店进行。菜品简单、朴素、实惠。没有豪奢之味,没有丝竹之乐,没有鞭炮之音。风声,雨声,祝福声,与天地苍茫之景蒙蒙辉映。
我记得,我的初中就是在弥河西畔的西黑联中度过的,这家联中由附近的七八个村联合组成。1979年我升入初中后,中央经过“拨乱反正”,教育秩序基本恢复。那时崇尚学识的母亲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鼓励我考取大学,向上发展。
初中的三年光阴短暂而充实。中午住校,母亲会将家中最好的“干粮”放在我的书包里。这期间,我恶补着失去的小学五年知识,其实,我真正的人生一年级,是从初中才正式开始的。
十七岁这年,我考取大学,成为小村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一位本科生。在我离乡之后的三十三年里,每年我都经历双亲送儿离乡的那一幕。年复一年,如今父母在村头招手离别的场景已成为半百之我铭记在内心深处的乡村图腾。
(七)
美好的日子总是幸福而短暂,一周时光转瞬即逝。这段有亲情陪伴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能听到父亲哼唱着小曲,母亲则欢快地进进出出,尽量将小院种植的小葱小菜摆上案桌。
这七日时光也是我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我走过田间垄头,跨越小沟小径,拨开荆棘丛杂,努力去觅寻着记忆中那点点滴滴的痕迹。这个不大的村落,像一泓清塘,承载了我多少绵绵不绝的乡愁。白云从树梢轻轻飘过,小鸟绕着屋顶圈圈飞翔,湾畔老槐树上花香四溢,静静的村落,就这么朴素自然。
从寒窗苦读到生存打拼,从一无所有至事业中天,从“少小离家”到“老大还归”,人生似圆,有时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样想着,一种生命沧桑感缓缓覆盖了忧忧的心田。我曾多少次问自己,哪里才是我生命的真正归宿?肉体享受抑或灵魂的修养?荒塚暗居抑或天堂的超然?
今天,我就要离开家乡了,济南的亲友已经来到小村接我。
“娘,我要回去了。”每次都是这句简单而低沉的告别。骨子里的我,从小就没有更多的蜜语甘言去安慰父母什么。
环顾温馨而又熟悉的小院,老屋,小门,枣树,翠竹,篱笆墙,还有茂茂密密的几畦青菜,还有庭台下大摇大摆的花猫,一切自然,亲切,安怡,令人依依不舍。
我走了,马达声告诉我,车已经离开。我不忍心回头看着父母苍老的身影,怕涌出泪水。但父母一定还站在马路中间挥手致别,一直望着小车绝尘而去……
 手机版
手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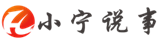 |
文化
|
文化






